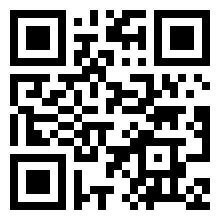特别报道︱我会副会长寿德俊文章《青砖缝里的茶香》在闽北日报发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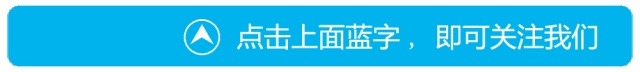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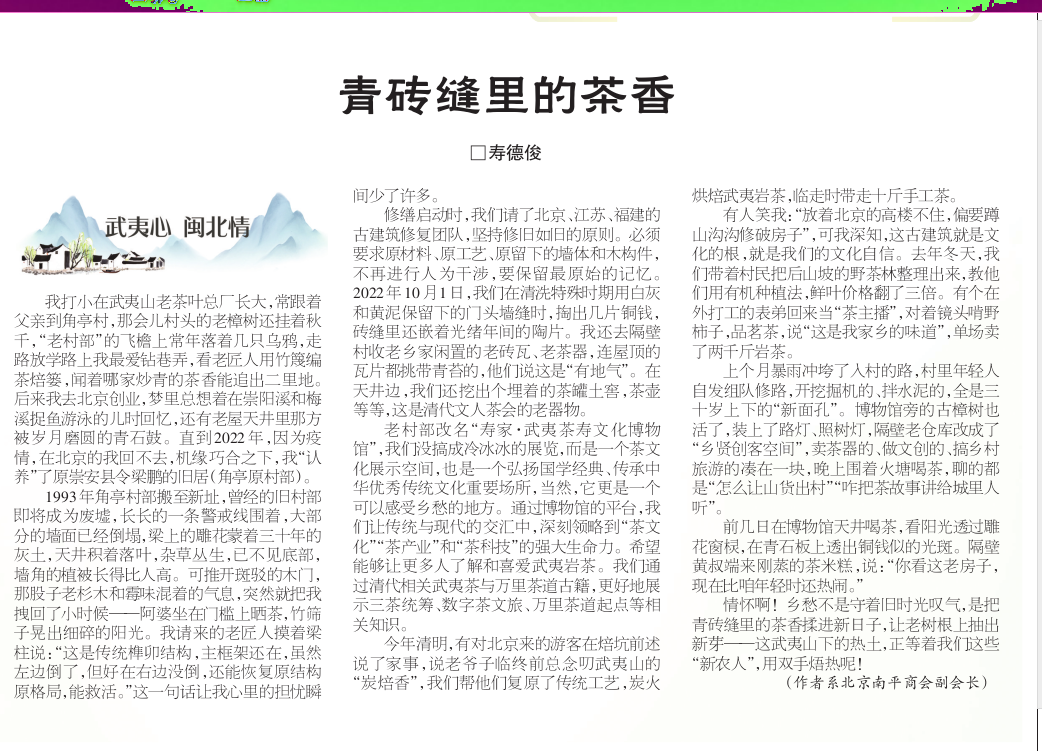
青砖缝里的茶香
寿德俊
我打小在武夷山老茶叶总厂长大,常跟着父亲到角亭村,那会儿村头的老樟树还挂着秋千,“老村部”的飞檐上常年落着几只乌鸦,走路放学路上我最爱钻巷弄,看老匠人用竹篾编茶焙篓,闻着哪家炒青的茶香能追出二里地。后来我去北京创业,梦里总想着在崇阳溪和梅溪捉鱼游泳的儿时回忆,还有老屋天井里那方被岁月磨圆的青石鼓。直到2022年,因为疫情,在北京的我回不去,机缘巧合之下,我“认养”了原崇安县令梁鹏的旧居(角亭原村部)。
1993年角亭村部搬至新址,曾经的旧村部即将成为废墟,长长的一条警戒线围着,大部分的墙面已经倒塌,梁上的雕花蒙着三十年的灰土,天井积着落叶,杂草丛生,已不见底部,墙角的植被长得比人高。可推开斑驳的木门,那股子老杉木和霉味混着的气息,突然就把我拽回了小时候——阿婆坐在门槛上晒茶,竹筛子晃出细碎的阳光。我请来的老匠人摸着梁柱说:“这是传统榫卯结构,主框架还在,虽然左边倒了,但好在右边没倒,还能恢复原结构原格局,能救活。”这一句话让我心里的担忧瞬间少了许多。
修缮启动时,我们请了北京、江苏、福建的古建筑修复团队,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。必须要求原材料、原工艺、原留下的墙体和木构件,不再进行人为干涉,要保留最原始的记忆。2022年10月1日,我们在清洗特殊时期用白灰和黄泥保留下的门头墙缝时,掏出几片铜钱,砖缝里还嵌着光绪年间的陶片。我还去隔壁村收老乡家闲置的老砖瓦、老茶器,连屋顶的瓦片都挑带青苔的,他们说这是“有地气”。在天井边,我们还挖出个埋着的茶罐土窖,茶壶等等,这是清代文人茶会的老器物。
老村部改名“寿家·武夷茶寿文化博物馆”,我们没搞成冷冰冰的展览,而是一个茶文化展示空间,也是一个弘扬国学经典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场所,当然,它更是一个可以感受乡愁的地方。通过博物馆的平台,我们让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,深刻领略到“茶文化”“茶产业”和“茶科技”的强大生命力。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武夷岩茶。我们通过清代相关武夷茶与万里茶道古籍,更好地展示三茶统筹、数字茶文旅、万里茶道起点等相关知识。
今年清明,有对北京来的游客在焙坑前述说了家事,说老爷子临终前总念叨武夷山的“炭焙香”,我们帮他们复原了传统工艺,炭火烘焙武夷岩茶,临走时带走十斤手工茶。
有人笑我:“放着北京的高楼不住,偏要蹲山沟沟修破房子”,可我深知,这古建筑就是文化的根,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。去年冬天,我们带着村民把后山坡的野茶林整理出来,教他们用有机种植法,鲜叶价格翻了三倍。有个在外打工的表弟回来当“茶主播”,对着镜头啃野柿子,品茗茶,说“这是我家乡的味道”,单场卖了两千斤岩茶。
上个月暴雨冲垮了入村的路,村里年轻人自发组队修路,开挖掘机的、拌水泥的,全是三十岁上下的“新面孔”。博物馆旁的古樟树也活了,装上了路灯、照树灯,隔壁老仓库改成了“乡贤创客空间”,卖茶器的、做文创的、搞乡村旅游的凑在一块,晚上围着火塘喝茶,聊的都是“怎么让山货出村”“咋把茶故事讲给城里人听”。
前几日在博物馆天井喝茶,看阳光透过雕花窗棂,在青石板上透出铜钱似的光斑。隔壁黄叔端来刚蒸的茶米糕,说:“你看这老房子,现在比咱年轻时还热闹。”
情怀啊!乡愁不是守着旧时光叹气,是把青砖缝里的茶香揉进新日子,让老树根上抽出新芽——这武夷山下的热土,正等着我们这些“新农人”,用双手焐热呢!